阿婆诞辰130年:“英式谋杀”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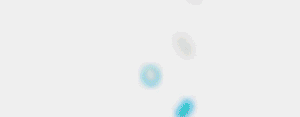
今天是英国侦探小说家、剧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在侦探小说的阅读仪式中,看上去有罪的人通常被证明是无辜的,罪犯隐藏在背后。我们试图借此逃离现实,回到一个想象中的原始的、单纯的、有秩序的世界。英式谋杀还是中产阶级荒谬性的象征:
他们用极端的行为来维持现状,宁愿犯罪也不愿因丑闻而丧失社会地位;稳定体面的生活之下隐藏着欲念,舒适生活与暗藏杀机之间充满悖论。
侦探与推理是受众最广的小说形式之一。作为“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堪称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作家,她的推理长篇小说有66部,此外还有大量短篇中篇小说选集和剧本,作品总销量超过20亿本。将她所有形式的著作算入,只有《圣经》与威廉·莎士比亚著作的总销售量能出其右。
 英国侦探小说家、剧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
英国侦探小说家、剧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
在英国侦探小说家多萝西·赛耶斯看来,侦探小说的形式之美,在于它拥有亚里士多德式完美的开头、过程和结尾,具有完美无缺的古典式结构,而犯罪和挑衅事件允许本我的冲动产生假想的满足。
推理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作家、最出色的侦探小说评论家西蒙·塞耶斯在他著名的评论集《血腥的谋杀》一书中还写道,侦探小说和俄狄浦斯神话存在着相似之处:显赫的受害者、初步的谜团、偶然的爱情元素、逐渐被披露的过去、最不可能的凶手。在侦探小说的阅读仪式中,看上去有罪的人通常被证明是无辜的,罪犯隐藏在背后。我们试图借此逃离现实,回到一个想象中的原始的、单纯的世界中。我们阅读犯罪小说的基本动机,还与宗教情节有关。
W.H.奥登在《侦探小说的秘密》中就认为,侦探小说有一种神奇的功能,“它的镜像就是找寻圣杯”,信仰光明之神与黑暗之神,即侦探和罪犯,在带有二元论清晰秩序感的世界中永无休止地斗争。侦探能嗅出腐蚀社会的坏人的味道,看透各种伪装,穷追到底,让正义得以伸张。
 1974年版《东方快车谋杀案》海报
1974年版《东方快车谋杀案》海报
阿加莎主要是在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岁月创作和成名的。在这个“黄金时代”里,侦探小说家对解谜推理推崇备至,智力游戏是首要目的。奥斯汀·弗里曼在《侦探小说的艺术》中指出,侦探小说绝不能同“纯粹的犯罪故事”相混淆,允许一定的幽默、人物描写和独特场景,但这些必须是“次要的、从属于智力上的兴趣的”。侦探小说的人物“仅仅是满足逻辑思辨的需要”,因为任何深入的描绘都会“在叙述中形成阻碍”。
那个时候普遍遵循的“推理十诫”,被视为“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写作戒律,就像智力游戏的竞技规则,确保了作家与读者之间能够公平竞争。这些戒律包括:凶手必须早在故事的前半段出场亮相,他的思考脉络不能被读者一览无余;绝对不可存在超自然的力量或媒介;只允许有不超过一个的秘密暗示或暗道;禁止使用尚未发明制造的毒药,也不可利用繁复难懂、需要长篇解说的器械工具犯案;不可靠妙手偶得,或利用无法解释却又正确的直觉破案;侦探自己绝对不可犯罪;侦探不可特意着眼于无关案情的线索,以误导读者;侦探身旁的朋友“华生”,绝不可隐瞒思维,其智商最好在一般人的平均智力之下;禁止有双胞胎的设计,若有,必须一开始就告知读者等。
几乎所有的古典侦探小说都遵循某种几何结构:有人被谋杀了,谋杀是一个谜。凶手存在于确定的封闭空间或明确数量的当事人当中。在显而易见的杀人动机之外(比如遗产、复仇、灭口),还隐藏着被掩盖甚至被伪装的隐秘的人物关系和杀人动机。出于各种目的和考虑,每一位证人对谋杀案的叙述都有欺骗和隐瞒。一位智慧的侦探将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和对人性的超凡理解,重构犯罪的过程,让读者看清躲避在思维盲点之外的真凶,真相的揭露通常出人意料。

《东方快车谋杀案》剧照
1920年,阿加莎发表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标志着“黄金时代”的正式发轫。这部小说算不上阿加莎最好的作品,在叙述上也颇为啰唆,但却开创了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侦探小说被认为是纯粹而复杂的谜团,对人物命运的关注是不需要的”,“无论故事背景是纽约还是英国乡村,书中的世界始终是一个稳定平衡的乡村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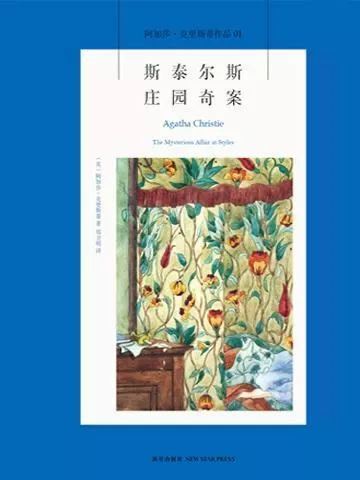
令阿加莎声名鹊起的杰作《罗杰疑案》(1926),才是一部有着完美几何结构的小说。它显示了阿加莎精巧绝伦的小说技巧,如钻石般,在每个小平面上都闪耀着纯净的光芒。小说的叙述者谢泼德医生的性格符合规则的模糊不清,他的沉默寡言偶尔呈现出自我控制和隐藏着的内疚。他是调查诈骗案与谋杀案的波洛身边的助手,他有很多观察与独白,还记录下了波洛每天的调查情况。他以带有怀疑精神的眼光打量着被害者罗杰身边的男女用人和家人,事无巨细地叙述着他和其他所有人在罗杰被害当晚的行踪。案情几度改变方向,我几度以为自己接近了谜底,几条可疑线索似乎都提供了可能性的指向。但当最终的谜底被揭晓时,我大吃一惊:谢泼德医生竟然才是真凶。
我所读到的一切都出自一个谜底知晓者的叙述,而我完全浑然不觉。只有当回过去重新再读时,那些自然得行云流水、丝毫不可能令人生疑的坦诚叙述才呈现出它们双重含义的另一面。他早已忠实而一丝不苟地讲述了自己的作案过程,公正不阿地遵循了“公平竞争”的规则,但阿加莎精彩绝伦的几何与数学技巧,让所有的谜底都遁形在并无欺骗却很迷惑人的凶手自述中。
甚至在小说一开头,谢泼德就已暗示道:“说实话,我那时相当沮丧,忧心忡忡。当时我不可能预见到接下来几周的风波——我绝对不会那么做——但直觉却告诉我接下来的日子麻烦重重。”可是,直到谜底揭晓,没有人会听出他胆大包天的话外音来!

电影《难补情天恨》剧照 (1979)。剧中阿加莎(瓦妮莎·雷德格瑞夫饰演)在接受因小说《罗杰疑案》的成功而授予她的荣誉
读遍各家侦探小说的朱利安·西蒙斯对阿加莎设计谜团的天赋评价极高,认为她“在迷惑人的诡计方面无人能及”。无论是《ABC谋杀案》(1936),还是《尼罗河上的惨案》(1937),抑或是《无人生还》(1939),阿加莎都在古典侦探小说的谜团和悬疑设计上,以其稳定的几何结构和前所未有的开创性情节,呈现了“黄金时代”所能孕育的最瑰丽想象。她就像个魔术师,“她先将黑桃A翻开给我们看,然后她把它翻过去,但是我们仍然知道它在哪里。那么,它是怎么变成方块5的呢?”这就是阿加莎的成就。

电影《无人生还》剧照 (1945)
那段岁月里,英国失业人口上升到300万,美国则在经济萧条后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消沉期。但这一切社会与历史现象都在侦探小说中找不到痕迹。小说中从来没有大罢工,也不存在工党;对穷人的同情并不是针对失业者和工人阶级,而是针对靠固定工资艰难生存的人。在这个童话国度里,发生着一个接一个的谋杀案,却没有现实的伤害。
就像一位侦探小说家在1930年准确预见的那样:“简单纯粹的犯罪解谜,完全仰赖情节设计而不擅角色塑造的小说时日,已经落在审判者的手中。侦探小说已到了一个阶段,未来侦探或犯罪的小说,吸引读者兴趣的心理层面,将超过数学成分。”
到了1946年,乔治·奥威尔就在他的《英国式谋杀的没落》一文中提问:“究竟是什么样的谋杀,对你的口味?”噢,这是个关键问题,谋杀也得以艺术眼光来审视。若无风格与审美,侦探小说也就与游乐园里链条和轨道上的机械装置并无不同,也不会成为一种文学形式和精神创造了(尽管人们对侦探小说家的文学成就时常争论不休)。
奥威尔是现实主义的,他冷峻地审视伪善的真实世界。他喜欢阅读《世界新闻报》上的谋杀案。那时的现实世界涌现了一批名声经受住时间考验的谋杀犯,包括格鲁利的帕尔默大夫、“开膛手”杰克、克里彭大夫、塞顿、约瑟夫·史密斯、阿姆斯特朗、拜沃斯特和汤普森。
这些谋杀案具有一些“英国性”:10名罪犯中,就有8人属于中产阶级。除两起以外,在其余所有案件中,性都是最重要的动机。至少在4起案件中,社会地位——想在生活中得到一个安全的位置,或者说不想因为离婚这样的丑闻而丧失原有的社会地位——是导致谋杀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半以上的案件中,犯罪的目的是得到确定数额的钱款,比如一笔遗产、一张保险单,但涉及的钱款数额相对不大。绝大多数案件中,犯罪行为都是随着侦查的深入而逐渐败露的,最初的怀疑对象要么是死者的邻居,要么是死者的亲属。
 《控方证人》剧照
《控方证人》剧照
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都存在某种戏剧性的巧合,天意清晰可见。那个时代的英国,社会快速变迁,现实能比小说精彩,有些谋杀的情节连小说家都不敢编造。比如,克里彭大夫把他不愿离婚的妻子的尸体藏在地窖里,与他装扮成男孩的情人横渡大西洋。又比如,当约瑟夫·史密斯用风琴演奏“我离你更近了,我的上帝”时,他的妻子正在隔壁房间里溺毙。这些犯罪的背景,几乎全部都在家庭内部;12个受害人中的7个,不是凶手的妻子,就是凶手的丈夫。
阿加莎·克里斯蒂与奥威尔其实属于同一时代的人,他们阅读着同样的社会新闻。那些谋杀可不是虚构小说营造的纯粹智力游戏王国,而是现实世界。在阿加莎以“韦斯特马科特”为名所写的半自传小说《半成画像》中,她透露,她曾短暂地害怕过第一任丈夫阿奇可能会犯下克里彭医生的谋杀罪。1926年,阿奇告诉阿加莎他爱上了别的女人,要求离婚。
如果阿加莎的小说仅仅是“黄金时代”规则下的古典智性游戏,也许她的名字也就像与她同时代的很多同样出色的侦探小说家(比如埃勒里·奎因、约翰·迪克森·卡尔、多萝西·塞耶斯、玛格丽·阿林厄姆等人)一样,逐渐遁入过去的世界,不再被公众提及。
阿加莎没有局限于清规戒律,她也是“英式谋杀”的写作典范。居于这类“英式谋杀案”核心的,是一种若无其事的常态:杀人犯会站在自己别墅的大门外,向邻居问候致意,谈论自己已被谋杀的妻子或丈夫。重大犯罪多半的吸引力和部分的恐怖,均非由于不正常的东西,而是因为其中正常的东西。
英式谋杀的魅力,恰在运转如常的生活和其内部看不见的可怕裂痕之间的张力。这种平常中的不寻常潜流,比显而易见的直白暴力、惊悚、恐怖或血腥更加含蓄和令人着迷。这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所构建的侦探小说王国的基调。她把真实的死亡变成故事,使它显得与现实遥远,并给它穿上双排扣礼服、戴上礼帽装扮起来;她聚焦于日常事务,为的是突出一天当中不寻常的那一刻,也就是那个精心隐藏起来的罪恶之谜。这就是阿加莎式的“舒适谋杀”:《啤酒馆谋杀案》里的真凶逍遥法外,恣意而体面地活着,只有波洛知晓她的死灵魂;《魔手》里的凶手有着令人尊敬的职业和社会地位,因而从不曾引起人的怀疑,他深藏自己的情感图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出轨企图,表面上正常得不能再正常。
阅读她的小说,她对英国乡村世情描写的趣味,甚至毫不逊色于她的侦探情节:《谋杀启事》里的茶间闲话,《藏书室女尸之谜》中马普尔小姐有点势利味儿的评弹淑女和下层女孩的穿着,《罗杰疑案》里的流言蜚语和麻将夜,《帷幕》里对旧世界的乡愁和现代的庄园生活,马普尔小姐嘴里圣玛丽米德村的家长里短、织毛线种花草……读着她的小说,有时我会想:“要是有个壁炉,烧着温暖的火焰”就好了,手边如果还有一壶红茶,配着德文郡的精美点心,那就更完美了——她的小说就是这样的令人舒适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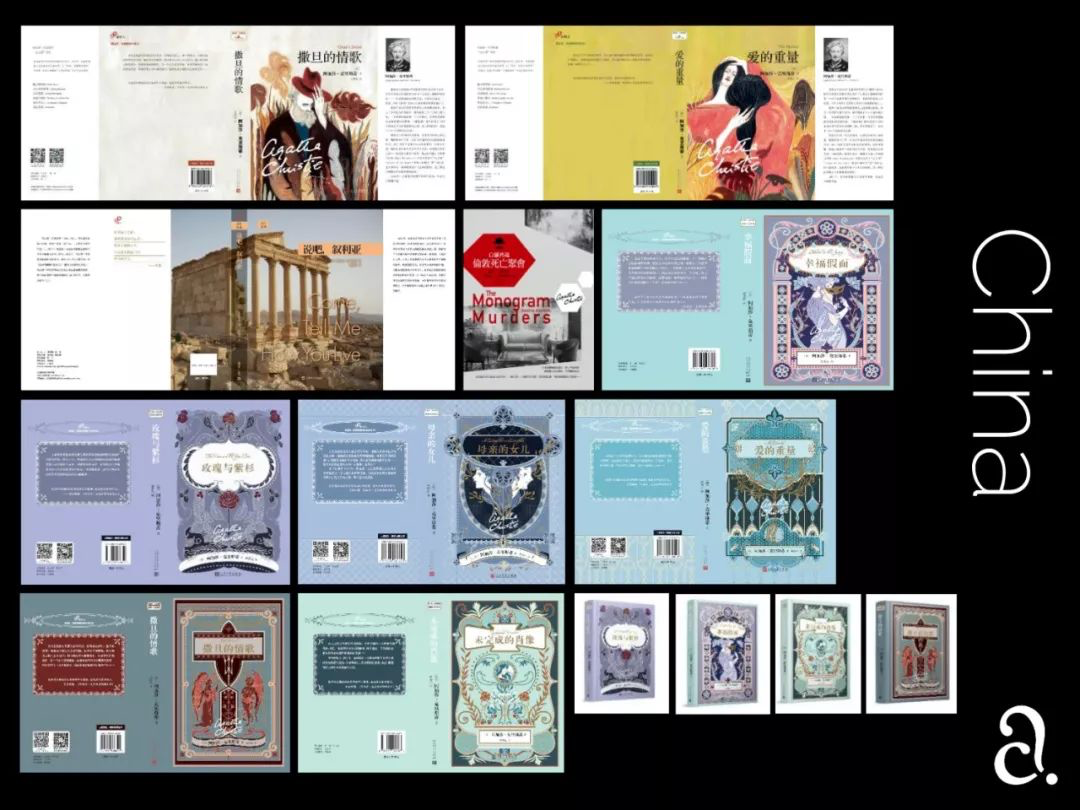
不仅是“舒适”,阿加莎的小说里还有一种对秩序世界的迷恋。那个稳定世界中的人们信仰体面,有人伪善犯下了罪行,希望掩人耳目,保住体面;但谋杀还是为秩序造成了混乱,最终由侦探抓到真凶,恢复秩序。侦探小说这种文体结构,为人们对秩序的心理需求提供了一种支撑,在阿加莎·克里斯蒂所经历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尤为显示出力量。
在侦探小说里,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不是凭借超自然的手段,而是靠勇气和智慧——你总是可以相信侦探波洛和马普尔小姐,他们让我们以为身处一个可控的、确定的世界里——无论经历多少的曲折甚至误判,你总是确定,他们一定能解决谜题,找到真实的答案。他们是新时代的英雄人物。
 1974年版《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的造型
1974年版《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的造型
阿加莎在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1934)、《死亡约会》(1938)、《无人生还》和《帷幕》(1975)都探讨了公正与合法性这个棘手的问题。她试图在一个想象的纯净世界中去解答它,去建构秩序。一个谋杀小孩的恶犯,因司法的不公正而逃脱了本应受到的制裁,孩子的亲属有没有权利伸张正义?一个习惯像监狱长看守犯人一样规训子女的家庭暴君,她看似意外的死亡对身边的人都是一种解脱,这样的谋杀是否是可以被接受的?一些人在日常生活中犯下了不为人察觉的罪行,比如故意见死不救,由于缺乏证据,在法庭上根本不可能受到起诉,他们是否应该受到审判?
阿加莎笔下的波洛和马普尔小姐,在谴责谋杀方面都是毫不含糊的。波洛常说:“我不赞成谋杀。”在1939年的《牙医谋杀案》中,银行家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向波洛申辩说,他是为了他的祖国而犯谋杀罪的,也应当因同样的理由被饶恕。“如果我死了,你知道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人需要我,波洛先生。而一个该死的杂种、敲诈勒索的希腊流氓却要毁掉我毕生的事业。”波洛信仰保守派清偿能力的政治信条,害怕没有他们的世界,然而当他说到布伦特仍要被问责的时候,他说:“我不关心国家,先生。我关心的是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他们有权不让别人拿走他们的生命。”
阿加莎的正义,是站在活着的人们的一边的,她绝不宽宥谋杀者,“宽宥他们无异于宽宥那些从中世纪瘟疫流行的村庄中出逃而混进邻村无辜村民和活泼孩子中的人。无辜者必须受到保护,他们应该能在平静和博爱中和睦相处”。
她书中的侦探摆脱了道德相对论的谄媚,提供了和谐与秩序、乐观主义的绝对道德范例。唯有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判定杀人情有可原;唯有在《无人生还》中,充当审判者的法官按童谣在孤岛上谋杀了九个有罪之人,并把这种夺人性命的私人审判变成了一种杀人的艺术——这也许是阿加莎最恐怖的一本小说。
最令人难以接受的,要数波洛临终前所破的那起谋杀案。在向世人告别的《帷幕》里,他以矛盾的心态,亲手处决了一位用心理手段诱使人谋杀的恶魔。在给好友黑斯廷斯的遗言中,他写道:“我不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我不相信一个人应该把法律掌握在他自己手里。但是另一方面,我就是法律!通过拿走他的生命,我拯救了其他人的生命,无辜的生命。但是我仍然不知道……我一直都这么自信,过于自信了。但是现在我很谦卑,我像小孩子一样说:我不知道……”

两次世界大战的那段岁月,侦探小说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14年前,古典侦探小说和外部世界相当一致。庞大的乡村别墅还矗立着,里面满是来访的亲朋好友,适度的乡村消遣、射击和垂钓,一众仆人和各式房间。这个世界在1939年以前就消亡了,但侦探小说家假装它依然存在,成了明显自欺欺人的游戏。“二战”结束时,古典侦探小说所带来的安慰已经变得不可靠,社会阶级构成和宗教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不再是岿然不动的。阿加莎胜于杰出同辈侦探小说家的活力,就在她并未囿于古典主义,而是直面更广阔的现代世界,以其丰沛的想象力,不断拓展侦探小说赖以生存的环境与空间。
她的童年在英国乡间的老宅阿什菲尔德度过,那是她一生魂牵梦萦的地方,也是“英国式谋杀”稳定舒适的乡村背景。幼年时代,她在巴黎见识了冠冕堂皇的旧式上流社会。在那儿,她父亲的美国国籍给她带来很多社交上的便利——所有的美国人都被认为是有钱的,而当时美国姑娘最受人欢迎,法国的贵族最愿意与美国富翁的千金缔姻。她学会了客套的礼貌言辞,学会了跳舞和得体举止,通过社交场上的朋友,了解到华盛顿、波士顿的一些事情和遍布世界各大都市的社交界。这些都成为她在《人性记录》(1933)、《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将侦探小说嵌入上流社会、都会社交圈和美国家族的素材。

纪录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谜样人生》 剧照
她在“一战”期间做过药剂师,这使她对毒杀诡计近乎痴迷,她的小说中有83桩毒杀案,有些手法带有异国情调,如使用毒芹碱、胡藤蔓和蓖麻毒素。后来,她又多次游离了异国情调的东方——她母亲为她考虑结婚事宜时,首先将她带入的是埃及的英国社交圈;她也曾与两任丈夫一起,或作为帝国博览会巡视团成员,或作为考古队成员,踏访大英帝国广阔的地理版图——南非、中东、澳大利亚等等。

她是那个时代见识罕见、视野一流的女性作家,也让她的侦探小说开拓出无人能及的辽阔疆土:穿越叙利亚、巴尔干半岛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发生在埃及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以约旦古城佩特拉为背景的《死亡约会》,还有一望题目便知道坐标的《他们来到巴格达》(1951)。她还以考古学家的研究精神,将《死亡终局》设置在古埃及,凭借一个古代嘎教祭司的信,勾勒出一个鲜活的古埃及家庭。这本小说,就像《ABC谋杀案》一样,在侦探小说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将侦探小说的背景放入了历史的不同年代。正因如此,阿加莎的侦探小说也可以当作一部世情小说系列来品读:英国的乡村生活,欧美大都会的上流社交圈,遥远东方国家的古迹和风俗人情。解谜的趣味,总是镶嵌在不断变幻的社会与地理背景之中,趣意盎然,令人永不疲倦。

《尼罗河上的惨案(1978)》剧照
在她76岁时,作为中上阶级女作家,她竟在《无尽长夜》(1967)中,以工人阶级的一员迈克·罗杰斯的视角,叙述了一起谋杀,体现出她惊世骇俗的想象力和魄力。她晚年回到英国乡村生活的侦探小说,读起来则像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人口流动改变着乡村生活传统的紧密人际关系,别墅被现代化的设施所改造,同性恋的关系变得习以为常,现代女性也不再遵从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这些都进入了她的小说;但她的基调,又弥漫着对旧世界的眷恋,那些关于美好旧世界传统、责任、秩序和道德观的挽歌,仍幽幽回荡在文字深处。“黄金时代”悄然逝去,阿加莎却并未令人沮丧,持续了她的创作巅峰。

一些观点认为,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是卓尔不群的谜案,无须,也缺乏对情感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力。但其实,当她以最佳状态从事创作的时候,她的作品超越了侦探小说在人性探究上的惯常缺陷。在像《啤酒谋杀案》(1942)这样的小说中,情节与人物如影相随,密不可分,以致谜案破解的进程就是揭示人性的过程,而谜底又完全取决于所揭示出来的人性真相。
一个画家被杀,竟然是因为他的模特爱上了他,而他假装仍然爱她,是因为他想完成那幅毕生最好的画作。她无意得知他的爱已经消逝,在绝望、嫉妒与愤怒中谋杀。画家的妻子承担下谋杀的罪名不做辩解,是因误解而想掩护自己曾伤害过的表妹,她在狱中死去,却因追随挚爱的画家丈夫而获得了灵魂的安宁;而那个依然活着的画家的情人,却成了行尸走肉的死灵魂。在这部小说中,阿加莎提及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就如在《帷幕》中,她引用《奥赛罗》和圣约翰·欧文的《约翰·弗格森》一样。她探索让人物性格成为推动情节的力量,她漂亮地做到了,证明了侦探小说可以是一种文学。
隐藏在她纯净的谜案中的其他东西,还包括她在1926年的那次精神崩溃之谜。《底牌》(1936)中的奥利弗夫人说:“我有过一个威尔士保姆,有一天,她把我带到哈洛盖特镇,然后回了家,把我忘得一干二净。精神极不稳定。”《地狱之旅》(1954)的中心人物希拉里·克雷文,也许走到了离阿加莎生活的秘密中心更近的地方。她准备自杀,“已经受够了长期的病痛,受够了奈杰尔的背叛,以及背叛发生的那个残酷而无情的环境”。但是她没有自杀,而是采用了一个劫后余生的女人的假面具。“车祸发生之前24小时的事对我来说仍然很模糊”,她说。阿加莎曾写道,不管自杀的冲动有多么强烈,这种诱惑最终总是被抵制住的原因:“我愿意给你举一个实例。有一个人走到了某一个地方,要自杀。但是他在那里意外地碰上了另一个人,因此他没有达到目的,就走开了,活了下来。第二个人救了第一个人的命,不是说他必须这样做,或者这是他一生中很重要的事情,而仅仅是由于单纯的物理空间原因。”
1926年,阿加莎挚爱的母亲克拉拉在阿什菲尔德花园去世。她置身于母亲塞满了旧物的老宅里,被孤独的巨浪拍打,感到没有了母亲的世界寒冷而恐惧,唯等在西班牙的丈夫阿奇回来给她抚慰。然而,当阿奇出现时,他已变心。他宣布有了情人,决定与阿加莎离婚。阿加莎的世界在那时坍塌掉了:不久,她失踪了,她的汽车在离斯泰尔斯庄园数英里一条公路的沟渠旁被发现,11天后,人们才在约克郡哈罗盖特的水疗旅馆发现她。
这段失踪的经历,是阿加莎绝口不谈的禁忌,是她真正的“闲人免进”区,留下的只有铺天盖地的猜测与想象。但也许正是这段经历,为阿加莎的文字也渲染上了一层神秘的光晕,成为她后来的小说里一种难以捉摸却若隐若现的底色。正如比她小30岁的英国当代推理小说家P.D.詹姆斯所评价的那样:“她从来都没有真正从中恢复过来。我想任何关系的破裂——一个女人如此投入了那么多的情感,都是一种决绝的伤痛。因此,她以写书为乐,尽管其中有常规的打乱与颠倒,最终秩序总是能恢复。从无序当中带来秩序,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这或许映照了她自己的生活。或许每本书都是一种感情宣泄。所有的,小小的宣泄。”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位于英国伯克郡沃灵福德的居所
阿加莎总是在她的侦探小说中创造出瑰丽的谜团,开辟出令人掩卷回味的一条条解谜幽径。但她也许无法破解现实生活的真相谜团。小说家约翰·福尔斯在《紫檀塔》中写道:
“你的意思是说,侦探小说必须在结尾将一切都解释清楚?这是规矩吗?”
“是幻想。”
“那么,如果我们的小说不遵守幻想的文学规则,或许意味着它其实更真于生活吗?”
1975年,侦探波洛在小说中去世。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许多西方大报都发布了他去世的讣告,仿佛他已是一位与我们相伴多年的真实人物。1976年,在小说《神秘的别墅》中,马普尔小姐正式谢幕。随后,阿加莎·克里斯蒂也追随她的创造物,离开了这个世界。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3期封面故事《跟阿加莎.克里斯蒂玩一场谋杀游戏》)

登录后可评论.